曾经沧桑情犹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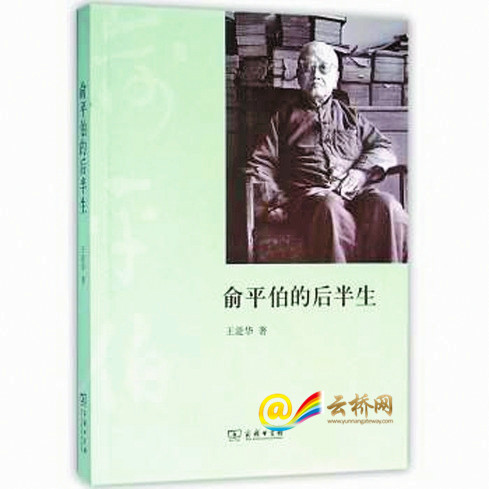
读完王湜华的《俞平伯的后半生》(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),掩卷思之,感触颇深。本书详述了俞平伯在1954年后思想、学术、生活等方面的经历,着重从他的学术生涯中,展现其精神世界和学者风采,深度剖析其治学与心境的巨大转变。作者王湜华乃俞平伯好友、著名历史学家王伯祥的哲嗣,故书中多有他与俞平伯的交往事迹的记叙,忘年之情感人至深。俞平伯后半生的个人经历,是他们那一代高级知识分子的缩影,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相连,历尽沧桑,备尝艰辛,但真情犹热。
本书一开始就以一篇《难以忘怀的1954年》作为俞平伯后半生的开端,俞时年55岁。也就是说,俞平伯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分界线是1954年。早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,作为正直的高级知识分子,俞平伯是想也是真心实意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服务,表现之一就是根据别人的意见,修改了他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专著,并将其由原来的《红楼梦辨》改名为《红楼梦研究》付梓出版。不料,1954年9月,以山东李希凡和蓝翎的《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》一文为开端,在全国掀起了批评《红楼梦》研究中唯心主义的运动,俞平伯首当其冲,成了批判的主要对象。这年10月16日,关于《红楼梦》研究的批判运动正式拉开序幕。俞平伯先后八次在批判《红楼梦》研究中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倾向会议上不断发言检讨。一时,以胡适为代表的“新红学”几乎成了反动的代名词,俞平伯的最大悲哀之一是后半生始终无法摆脱那个与胡适之间的“等号”。这场批判运动的名称叫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,具体落在《红楼梦》研究上,可胡适在国外,于是,俞平伯就成了近在眼前的靶子。批判除了写文章外,就是开会,俞平伯也被传唤到会。这一过程有两个后来也屡试不爽的做法,一个是俞平伯的讲话,先是叫发言,后来叫检讨;一个是对他的称谓,先是后缀以先生,后是直呼其名。这说明什么呢?说明俞平伯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,结局自然不妙。
“学术权威”俞平伯因为写了《红楼梦研究》被“小人物”李希凡和蓝翎逮住尾巴,又被上面领导重视,就和胡适挂起钩来,受到全国性的批判。但是,他和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终究有区别,在开始时可以继续参加社会活动,如1959年春加入了由人大和政协组织的到江南一带的巡视。他和老友叶圣陶等同行,最后一站是他们的老家苏州。可在将入苏州时,俞平伯独自离队去了南京。后来人们才知道,他是去鸡鸣寺凭吊亡友朱自清的。说起朱自清,我最先记起的是他和闻一多都有傲骨,闻是拍案而起,朱是不食嗟来之食,后来记起的就是他的散文,如《荷塘月色》《背影》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等。其实,俞平伯当年和朱自清同游秦淮河后,也写了一篇散文,和朱的题目一样。只是俞平伯在1949年后和朱自清的命运不一样,朱自清的那篇人们耳熟能详,而他的那篇就湮没无闻了。南京曾是六朝古都、金粉之地,进入民国后,那一带尤其是秦淮河畔,犹有旧时的流风余绪。朱自清和俞平伯作为青年学子,骨子里有着中国文人固有的做派,其荡舟秦淮河,吟咏风月是应有之举,文章自然也写得旖旎蕴藉,堪称美文。1949年后,俞平伯一直住在北京,离南京比较远,而那次巡视正好是江南一带,趁隙回转南京,甚是便利。何况亡友遗踪在旁,且思念切切,俞平伯就不愿错过了。在南京凭吊后,俞平伯也留下了文字。
1966年夏,俞平伯这个早在12年前就被批判的“反动派”自然难免抄家。其外孙韦柰所写《俞平伯的晚年生活》(1990年第4期《新文学史料》)中有详细的描述,包括俞平伯夫人许宝驯被剃阴阳头,其母被穿上寿衣,俞平伯夫妇被强迫跪在地面,作号哭状。随后是干校、地震……二十多年艰难岁月,俞平伯夫妇以豁达心境共同熬过。可惜许宝驯夫人于1982年2月先谢世,六十四载岁月,俞平伯看似表面镇定,实则早已欲哭无泪形同木立了。许宝驯夫人生病住院时,俞平伯就写了22封信给她,及至去世后,20首悼亡诗足表心迹,不忍卒读。关于丧事,俞平伯主张从简,骨灰安放在卧室内。1977年,俞平伯早已酝酿的纪念结婚六十周年的长诗《重圆花烛歌》让人动容,长诗也算六十年来往事的某种形式的回忆。通过他内弟许宝骙《俞平伯先生<重圆花烛歌>跋》可以知道,在这类似传记的长诗中,未提一字《红楼梦》,只因他后来不愿意别人叫他“红学家”。
1990年10月15日,俞平伯临终前用颤抖的手写了勉强能辨认的字,一纸写:“胡适、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,有罪。程伟元、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,有功。大是大非!”另一纸写:“千秋功罪,难于辞达。”回首再看当年批判种种,于心何忍。当年俞平伯写完《红楼梦辨》后,书稿两次失而复得,冥冥之中似有命运的安排,若无这样的安排,他的后半生也不至如此了。
作者:毛本栋